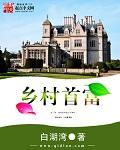笔趣阁>明末我崇祯摆烂怎么了?!最新章节免费 > 第321章 黄河就是这样不治理会出事治理也还是会出事(第2页)
第321章 黄河就是这样不治理会出事治理也还是会出事(第2页)
他下令将钟吊出封存,并在石室四壁涂抹石灰,焚香驱秽。临走前,他在钟基底部发现一行极小的刻字:
>“第八代,以万民之信为养料,以乱世之怨为引火,待时而动。”
消息传回宫中,王兴隆听罢,久久不语。良久,他命人取来一幅天下舆图,铺于床前,用枯瘦的手指缓缓划过黄河、长江、辽东、云南……
“骆养性。”他忽然开口,“你说,如果我现在下诏,宣布自己并非朱家血脉,而是普通百姓之子,这江山还会不会乱?”
骆养性大惊:“陛下何出此言!”
“我只是想试试。”王兴隆苦笑,“看看人们忠的是‘皇帝’这个人,还是‘皇帝’这个名号。若我坦白一切,他们是否会立刻反戈相向?还是会说‘哪怕你不是真龙,我们也愿跟着你走下去’?”
骆养性沉默片刻,低声道:“臣不敢欺君。多数人或许会动摇,但必有一部分人,因您十七年勤政爱民,而选择继续追随。而这部分人,才是真正的国本。”
王兴隆点头,眼中闪过一丝欣慰:“那就够了。”
数日后,朝廷突然发布一道奇特诏令:在全国设立“自省碑”,凡百姓皆可前往刻写对朝廷的不满、对官员的控诉、对政策的质疑,内容不限,匿名可署名亦可,每月由御史汇总呈报皇帝亲阅。
此举震惊朝野。内阁首辅跪谏:“此乃动摇君威之举!”
礼部尚书痛哭流涕:“祖宗之法,天子神圣不可侵犯,岂容庶民随意评议!”
王兴隆只回一句:“若朕连几句骂都听不得,还算什么治世之君?”
于是,“自省碑”遍立城乡。起初,碑上尽是谩骂诅咒:“皇帝昏庸!”“税重如牛!”“锦衣卫如虎!”
可渐渐地,也出现了其他声音:“去年免粮,救我家五口性命。”“屯田营给我饭吃,给我地种。”“女儿上了义学,会写自己的名字了。”
更有甚者,在碑旁自发搭起茶棚,供人歇脚饮水,名为“听骂亭”,掌柜自称曾是赤旗军余党,如今悔过自新,愿以劳力赎罪。
一年过去,某县自省碑竟被磨平三次,不得不换上铁碑。地方官上报称:“百姓已不再只知抱怨,开始讨论如何改进水利、修桥铺路,甚至提议合村联防防盗贼。”
王兴隆听后,终于露出久违的笑容。
然而,暗流从未停歇。
江南某小镇,一间私塾夜晚灯火通明。小玉站在讲台上,面前是一群十一二岁的孩子。墙上挂着一幅手绘地图,标注着“景山”“钟楼”“地宫”等字样。
“你们知道吗?”她轻声说,“真正的历史,从来不在官府写的书里。而在那些不肯闭嘴的梦里,在那些烧不完的纸钱里,在每一个记得‘白发王者’的人心中。”
孩子们屏息聆听。
“建文帝没有死。他只是沉睡了。而唤醒他的钥匙,不是刀兵,不是皇位,是相信。”
“只要还有一个人相信,他就没有真正消失。”
“而那个人,也许就在你们中间。”
话音落下,屋外雷声骤起,一道闪电劈中远处古槐,树干裂开,露出一块埋藏已久的瓷片,上面赫然印着半道龙纹。
同一时刻,北京皇宫,那本《转轮纪要》再次自动翻页,新浮现的文字冰冷如霜:
>“信仰之力已达临界。
>第八代容器,已完成初步人格融合。
>意识同步率:%。
>预计觉醒时间:三年内。
>触发条件:大规模饥荒或战乱。”
王兴隆躺在病床上,手中握着最新一期《民声集》,目光停留在一则边疆奏报上:
>“蒙古诸部蠢动,或将于明年春犯边。
>加之去岁北方少雨,麦苗枯萎,恐酿大饥。”
他缓缓合上册子,望向梁顶蟠龙雕饰,轻声道:“又要来了么……”
窗外,钟声准时响起,第十二声余音未散,一阵狂风突袭而至,吹熄了殿内七盏宫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