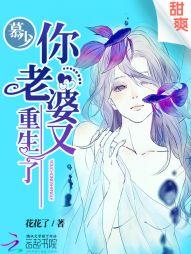笔趣阁>明末我崇祯摆烂怎么了?!无弹窗最新章节 > 第321章 黄河就是这样不治理会出事治理也还是会出事(第3页)
第321章 黄河就是这样不治理会出事治理也还是会出事(第3页)
三日后,王兴隆召集太子与重臣于乾清宫西暖阁,举行最后一次朝议。他虽虚弱不堪,却坚持坐起,亲自口述遗训十二条,涵盖边防、赋税、司法、教育诸项,条理清晰,字字千钧。
最后,他看向太子,郑重道:“朕死后,勿厚葬,勿立碑,只需在景山脚下立一小石,刻八字即可。”
“哪八字?”太子含泪问。
“宁负我者,不负苍生。”
众人无不垂首动容。
当夜,王兴隆服下一剂安神汤,沉沉睡去。梦中,他回到了十七年前的信王府,庭院梅花盛开,母亲正在教他读《资治通鉴》。她抬头微笑:“儿啊,做皇帝不容易,但只要心正,鬼神也不敢欺你。”
他泪流满面,想要扑上前去,却见母亲身影渐渐淡去,取而代之的是无数面孔:饿殍遍野的灾民、屯田营中挥锄的流寇、戏台下鼓掌的老农、烧纸钱的小宦官、学堂里的孩童……
他们齐声说道:“我们记得你。”
猛然惊醒,窗外钟声正响,第一声悠扬入耳,恰是五更天明。
他微微一笑,气息缓缓消散。
一代帝王,就此落幕。
七日后,太子登基,改元“承平”。大赦天下,追谥先帝为“敬宪皇帝”,庙号“思宗”。
但在民间,百姓私下称呼他为“实心皇帝”??因他批红用墨极重,奏章上字迹深陷纸背,仿佛每一笔都耗尽心血。
而那位白发孩童,自此消失不见。
景山地道被彻底填平,青铜小钟熔铸成一口铜鼎,置于天下书院门前,鼎上铭文曰:
>“信非盲从,智在求真。
>钟可乱耳,书能明心。”
多年后,有学者整理崇祯朝档案,偶然发现一份未归档的手札,纸页泛黄,笔迹颤抖,似临终前所书:
>“我始终不信天命,也不觉得自己是明君。
>我只是不愿在最后一刻,闭眼前看见的仍是百姓绝望的眼神。
>所以我选择了不停地做??哪怕无人知晓,哪怕注定失败。
>若后人问我为何坚持?
>我只能说:
>因为我活着的时候,还能选择去做点什么。
>这便是我对‘皇帝’二字,唯一的理解。”
手札末尾,无署名,仅盖一方私印,印文为:
**“一介凡夫,也曾扛过江山。”**
又三十年,天下再起动荡,边患复炽,民变频发。某夜,长安街头一群少年聚于废庙,点燃篝火,讲述旧事。
一人问:“听说从前有个皇帝,每天批奏折到天亮,手指冻裂也不停,是真的吗?”
另一人点头:“是真的。他还说,宁可天下负他,毋使他负天下。”
第三人仰望星空,忽然道:“你们有没有觉得……最近总做同一个梦?梦里有个穿青袍的人,背着个老人走在雪地里,鞋破了,脚流血了,可他一直没停下。”
众人默然。
远处,一口废弃的古钟,在月光下微微震颤,仿佛即将响起。
而在西北某座荒山上,一个白发少年缓缓睁开双眼,掌心龙纹熊熊燃烧,如烈焰腾空。
钟声,还未结束。